上海男士机械手表(上海男士机械手表价格)
■劳动报首席记者庄从周摄影展翔
1958年,上海表推出A581,这是该品牌第一款自制量产手表,彼时,报纸报道“千余人登记预约,争买首批上海牌手表,各地纷纷来信探问”。很多上海市民都把一枚上海表当成是传家宝,“这个表要戴一辈子的。”上海牌手表作为市民的回忆坐标,在历史的大潮中也曾经历起伏。如今,榆林路上海表业有限公司内,生产车间依然忙碌,国产的陀飞轮手表在师傅们的巧手之下,同样有着精准的走时。1986年,李文侠进入上海表业工作,一转眼已经快40年,正是他当年带领团队研制出国产陀飞轮机芯,让上海表跻身世界顶级腕表之列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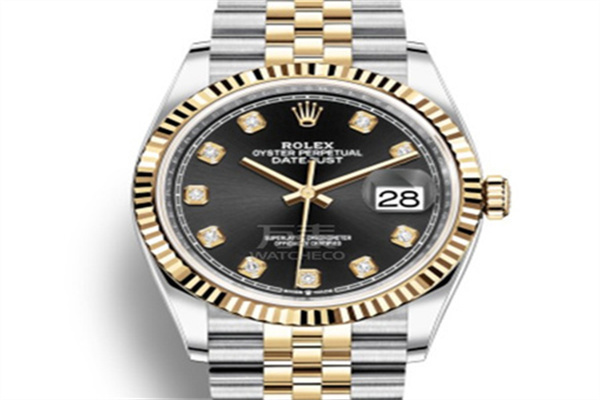
攻克最精密的陀飞轮
重量相当于一片鹅毛
对于爱表人士来说,陀飞轮是永远绕不开的话题。陀飞轮手表是全球公认的机械表之王。通过把整个擒纵调速结构组合在一起,以一定速度不断旋转,就能将地心引力对机械表“擒纵系统”的影响降至最低,从而提高走时精度。独特的运行方式,把计时精准度和动感美发挥到了极致。尽管工艺原理看似简单,但装配陀飞轮机芯却是世界级挑战。
装配车间主任李文侠告诉记者,20多年前,上海表还没有自己研制的陀飞轮机芯,他和团队成员都想攀登上这个手表行业的“最顶峰”。“陀飞轮装置里,有超过70多个精密的零件,他们全部需要手工组装,整体重量不超过0.4克,相当于一片天鹅羽毛的分量。”经过团队多年的努力,上海表的自制陀飞轮结构终于亮相。23年前,当新款的上海牌手表亮相于瑞士巴塞尔国际钟表展时,瑞士手表商对于中国钟表制造工业的创新能力赞叹不已。
如今,在上海表业2楼的装配车间里,李文侠带领着50位制表师傅,在表盘装配、机芯装配、成表检验这三个环节里,精益求精,力求让出厂的每一块上海表都能有着精准的报时和艺术化的做工。
装配车间寂静如诗
一盏明灯陪左右
李文侠带着记者走入装配车间时,需要通过强风吹拂的处理间,然后戴上工作帽。这些细节都在述说着,一块手表的制作工艺需要极高标准。
左右两间厂房,分别为机芯装配和表盘装配。这里非常安静,且几乎没有整体照明。走在昏暗的走道上,李文侠对记者说,“在这里,针掉在地上的声音真的可以听见。”在表盘装配车间,一位1977年便进厂的师傅正在用仪器检测表盘里配件的偏重度,戴着用于放大的眼镜,时刻观察仪器里不断变化的数据,以此调整到平衡的状态。这样的处理步骤,每天要重复几百次。
李文侠透露,最忙碌的时候,表盘装配车间的师傅们连上洗手间的时候都要有人顶上换班,“那是最辉煌的时候,全中国的老百姓都想拥有上海表的日子。”
如今,虽然手表行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,但对李文侠和进厂二三十年的制表师傅们来说,他们是择一事终一生的最好例子。就像昏暗的车间和头顶的那盏明灯,李文侠和其他师傅们一起坚守着属于上海牌手表的荣光,哪怕这个过程枯燥寂寥,就像一首冗长晦涩难懂的诗。
想让更多年轻人留下来
“哪怕坚持半年也好”
李文侠告诉记者,上海牌手表近年来在研制上不断突破,包括“轨道式裸摆、中心天轮式中置摆轮、二维立体陀飞轮”等机芯,许多都成了业内主流,部分还成为航空军用指定计时产品。但车间里,师傅们慢慢都变成了老师傅,而年轻人很难静下心坚守在岗位之上。“其实我带的几个徒弟,只要肯留下来,收入都是不错的。”李文侠说,制表行业开头难,一开始有长达半年的实习期,拿着最基本的工资,吃着常人难以想象的苦。“为此,一个又一个年轻人离开了。他们离开,我一点都不怪他们。”李文侠说,他只希望,有时候规则可以改一改,“让他们上手快的,先拿计件工资,不要卡死人家只有基本工资,让年轻人有一点收获感和满足感。哪怕坚持半年,能留下来的也就留下来了。”李文侠说道。
如今,通过“师徒带教”,李文侠渐渐培养了一大批手表装配维修骨干,团队中有25位晋级中高级工,8位在技能比武中崭露头角,更有多人在手表维修领域成为骨干力量。
李文侠表示,自己将继续精雕细琢国民腕表“中国芯”的每个零件、每道工序,用心做好时光的记录者,让上海牌手表这个传奇不断续写下去。
上海表业有限公司外景。
李文侠正在检测手表零件故障。
一位师傅在车间装配机芯。
劳动报抖音

还没有评论,来说两句吧...